 |
| 主 題:【書摘】《巨流河》/齊邦媛 | 點閱:1487 |
| 張貼者:alice | No Email |
| 書名:巨流河 作者:齊邦媛 出版社:天下文化 《巨流河》文摘 P58: 祖母的轎子走很遠了,還聽到我在哭,但又不能帶我走。有一次臨走時,她也哭了,眼淚在皺紋裡是橫著流的,至今我才明白何以古人文章裡說「涕淚橫流」……。(涕泗縱橫) p114: 地理科的吳振芝老師教初中的中國史,提到臺灣時叫我們記得「雞蛋糕」(基隆、淡水、高雄),我們就在背後叫她「雞蛋糕」。 p128: 烽火燒得熾熱,炸彈聲伴著我們的讀書聲。不跑警報的時候,埋首用功;跑警報時,課本仍然帶著,準備明天的考試。在這種環境長大的孩子,跟今天在幸福環境成長的孩子比起來,較具憂患意識,懂事得早,心靈卻也衰老得快一些。在那麼艱難的成長環境,我們每天吃得不好,穿得不好,晚上被臭蟲咬,白天要跑警報,連有月亮的夜裡也不放過。正因為如此,剩下的一點時間就變得無比珍貴,老師說:「不好好做人,就會被淘汰。」就像不好好躲起來就會被炸死那樣地戒慎恐懼。 p138: 父親一生常在我頗為自滿的時刻說:「可真不容易啊,但是……」引領我進入深一層思索,雖然當時有悻悻然之憑,但我一生處逆境時,多能在不服氣之後,靜靜檢討,實得之於父親的這種開導。 p144: 那天晚上,下起滂沱大雨,我們全家半坐半躺,擠在尚有一半屋頂的屋內。那陣子媽媽又在生病,必須躺在自己床上,全床鋪了一塊大油布遮雨,爸爸坐在床頭,一手撐著一把大油傘遮著他和媽媽的頭,就這樣等著天亮……。(好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杜甫) p148: 一般說來,文組的人是理科不行但文科也未必更好。(唉唷喂啊) P178: 這麼一位大學者(朱光潛)怎麼會召見我這個一年級生呢?說真的,我是驚駭多於榮幸地走進他那在文廟正殿,大成殿,森然深長的辦公室。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裡並不壯碩的穿灰長袍的「老人」(那一年朱老師四十七歲,我那時的年紀眼中,所有超過四十歲的人都是「老人」)也沒有什麼慈祥的笑容。 P178: 朱光潛老師對齊邦媛說: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沒有鑽研哲學的慧根。中文系的課你可以旁聽,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課程必須有老師帶領,加上好的英文基礎才可以認路入門…… P179: 爸爸對齊邦媛說:你感情重於理智,唸文學比較適合。 P183: 朱老師用當時全世界的標準選本,美國詩人帕爾格雷夫主編的《英詩金庫》,但武大遷來的圖書館只有六本課本,分配三本給女生、三本給男生,輪流按課程進度先抄詩再上課。 P184: 教到華茲華斯較長的一首〈瑪格麗特的悲苦〉(The Affliction of Margaret)(寫一婦女,其獨子出外謀生,七年無音訊。詩人隔著沼澤,每夜聽見她呼喚兒子名字……) 老師取下了眼鏡,眼淚流下雙頰,突然把書閣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滿室愕然,卻無人開口說話。 對於仍然崇拜偶像的大學二年級生來說,這是一件難於評論的意外,甚至是感到榮幸的事,能看到文學名師至情的眼淚。 P189: (借住旅店遭土匪來搶劫時,齊老師是唯一女性,躲在像棺材的錢櫃裡,另一位學長打開鋪蓋睡在上面) 我出來的時候,發現所有躺著的同學頭下都有幾本書。因為他們知道四川強盜都不搶書,「書」、「輸」同音,而且據說四川文風鼎盛,即使盜匪也尊敬讀書人。 P192: 所有初讀雪萊詩的年輕人都會被他奔放的熱情所「沖激」吧,愛情和死亡的預感常在一行詩中以三個驚嘆號的形式出現……(I die! I faint! I fail!) P193: 英國哲人羅素說:我愛他(雪萊)詩中的絕望、孤立和幻想景致之美。 p193: 朱老師堅信好文章要背誦,我們跟他唸的每首詩都得背。 p194 終於,這些狂炸我們八年的日本人,也嘗到自己家園被別人毀滅的痛苦,也知道空中災禍降臨的恐怖了。自侵占東北以來,他們以征服別人為榮,洋洋自得地自信著,他們家鄉的櫻花秋葉永遠燦爛,卻驅趕別的民族輾轉溝壑,長年流離! 我也無言無語,沉痛而歡欣地站在那石柱之前,想像一千八百架轟炸機臨空時遮天蔽日的景象,似乎聽到千百顆炸彈落地前尖銳的呼嘯,爆炸前灼熱的強風,房屋的倒塌和焚燒,地面土石崩濺的傷害,……啊,難以忘懷的青春歲月!死亡在日光月明的晴空盤旋,降下,無處可以躲藏!…… 那些因菊花與劍而狂妄自信的男人,怎樣保護那些梳著整齊高髻,臉上塗了厚厚白粉,大朵大朵花和服上拴著更花的腰帶,穿著那種套住大腳趾的高蹺木屐的女人,踢踢踏踏地跑呢?有些女人把在中國戰死的情人或丈夫的骨灰在背袋裡,火海中,這些骨灰將被二度燒……!(八年抗戰成功,這是向來溫文典雅的齊教授對日人所說的最沉痛控訴) p213 (寫給張大飛的信:) 很羨慕你在天空,覺得離上帝比較近,因為在藍天白雲間,沒有「死亡的幽谷」……你說那天夜裡回航,從雲堆中出來,驀地看到月亮又大又亮就在眼前,飛機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 P238 我記得常聽父親說:「一個知識分子,二十歲以前從未迷上共產主義是缺少熱情,二十歲以後去做共產黨員是幼稚。」我常想聞一多到四十五歲才讀共產制度(不是主義)的書,就相信推翻國民黨政權換了共產黨可以救中國,他那兩年激烈的改朝換代的言論怎麼可能出自一個中年教授的冷靜判斷? P243 我參加了張莘夫追悼遊行……但是我既未參加遊行籌備工作,又未在遊行中有任何聲音,只儘量地跟上隊伍,表達真正哀悼誠意,但是從白塔街走到玉堂街就被擠到路邊了。後來我自己明白,原來我不屬於任何政治陣營,如果我不積極參與活動,永遠是被擠到路邊的那種人。如果我敢於在任何集會中站起來說,「我們現在該先把書讀好」,立刻會被種種不同罪名踩死,所以我本能地選擇了一個輕一點的罪名,「醉生夢死」。 P261 上海是虛張聲勢的繁華。 p276 (楊端六教授與「前進」的女兒的對談:) 女兒說:「大學教育有什麼用?專門讀書有什麼用?一點不能和現實結合起來。」 父親說:「一個人不讀書怎麼能懂得世界上的事情,怎麼曉得分辨對與不對?人對於問題的看法完全要靠他的腦筋來判斷,而腦筋不經過讀書怎麼訓練?」 p287 整個中國都在非左必右的政治漩渦中,連鴕鳥埋頭的沙坑都找不到了。 P336 躲避球的打法,總覺得對人生有嘲諷的況味……它似乎不講究球技,只以擊中敵人數目定輸贏,是一種消極的運動。好像在擁擠的地方消滅過多的人,自己才能生存。我心中一直凜然於躲避球的人生觀,悲傷地看著那些孩子在操場的塵土裡四面躲避,以免被擊中出局。我希望普天下的孩子平安穩定地生長,不必為躲避災難而培養矯健的身手。 P351 在那五年中(台中一中教英文)每年暑假看大學聯考榜單也是我生命中的大事,好似新聘教練看球賽一樣,口中不斷地教他們不要想輸贏,心中卻切切懸掛,恨不能去派報社買第一份報紙。在那一版密密麻麻的榜單上用紅筆畫出自己的學生名字,五十年前和今天一樣,先找台大醫學院和工學院的上榜者,工學院又先找電機系,因為分數高。我不能自命清高說我沒有這份「虛榮心」。 P358 回台飛機上,坐在我旁邊的是一位美國老先生,問我許多關於台灣的問題,我都盡我所知地回答。他臨下飛機前給我一張名片:安德森博士,華盛頓美國大學校長。回台後,我再度回台中一中任教。當時的教育部長是張其昀,有一次他到台中來,通知台中一中宋新民校長,說要召見齊邦媛教員……張部長對我說:「安德森校長幾次演講都提到你,非常稱讚,說你們台灣的中學教員水準很高,教育部希望你到國際文教處工作。」 P366 胡先生(胡適)說自己的工作是介乎文學與歷史兩者之間的研究,寫感想時用的就是文學手法,他說:「感想不是只有喜、怒、哀、樂而已,還要有一些深度。深度這種東西沒辦法講,不過你自己可以找得到。如果你有,就有,沒有,就是沒有,但是可以培養。」……後來我給學生上課或演講,都覺得文學上最重要的是格局、情趣與深度,這是無法言詮的。 p369 Sister Frances(靜宜文理學院負責人)對學生很嚴格,舉凡儀容、用餐禮儀、生活常規都要管,她曾說:「女孩子打扮得乾淨、漂亮不是為了好看而已,而是為了禮貌。」 P391 (在中興大學時期) 二年級借用畜牧系一間緊靠牧場的教室。有一天我在上大英國文學史最早的史詩〈貝爾伍夫〉的時候,一隻漂亮的牛犢走進門來,我們雙方都受了驚嚇,幸好無人喊叫,牠終於好不容易地轉了身,由原門出去。事後畜牧系主任告訴我,那是剛進口的昂貴種牛,是為台灣改良農業的珍品,你對牠講文學,彼此都很榮幸呢。 P432 當初議會叫囂收回市產的時候,仍有一些史學研究的年輕學者前往素書樓探視,且為他(錢穆)整理、校訂舊作。錢先生問他們:「這些人急著要這房子做什麼?」他們說:「要做紀念館。」他說:「我活著不讓我住,死了紀念我什麼?」(一九六七年錢先生遷居台北,政府禮遇學人,助其在陽明山管理局賓館預定地上建一小樓,名「素書樓」,可以安居,講學著述,頤養天年。他萬萬想不到的是,晚年「歸」來定居的台灣竟也到了沒有溫情與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歲的高齡,一九九O年六月底,為尊嚴,倉皇地搬出了台北外雙溪的素書樓,落腳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兩個月後逝世。) P469 伍爾芙《自己的房間》,她的名句是:「一個女人想要從事文學創作,必須有錢和一間她自己的房間。」 P476 文學和玫瑰一樣,它的本質不因名字而改變。 P476 自從有記載以來,凡是在台灣寫的,寫台灣人和事的文學作品,甚至敘述台灣的神話和傳說,都是台灣文學。世代居住台灣之作家寫的當然是台灣文學;中國歷史大斷裂時,漂流來台灣的遺民和移民,思歸鄉愁之作也是台灣文學。 P479 那是個共同尋求定位的年代,都似在霧中奔跑,找尋屬於自己的園子。 p566 齊家祖填既已被剷平,我童年去採的芍藥花,如今更不見蹤影,而我也不能像<李伯大夢>中的Rip Van Winkle,山裡一睡二十年,鬢髮皆白,回到村莊,站在路口悲呼,「有人認得我嗎?」 p570 當年同班女同學到了十多位,見面都已不識,都是老太太了。只有在說出名字時驚呼一番,我們急速地把五十年前的影像延伸到眼前的現實,無數的「你還記得嗎?」都似在解答我在台灣難解的謎,驗證了我今生確曾那般歡躍活過的青春。這些人,這些事,那魚池,那梅林都真正存在過,歲月能改變,但並不能摧毀。 p574 政治和戀愛一樣,相處久了,就不能翻身。 繼續閱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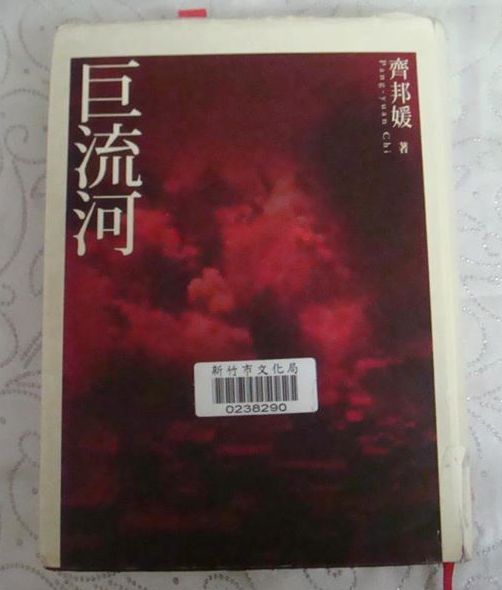 |
| 回【 教學手記 】 回【 上 一 頁 】 |